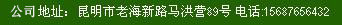|
摘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新闻出版法规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年首颁《大清印刷物专律》迄今,中国新闻出版法规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从“清末修律”时的雏形初显,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博弈抗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新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法规一直在不断演进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一以贯之的社会变迁线索,又有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背后是一条中国新闻出版法规的百余年制度演进逻辑。 关键词: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制度演进社会变迁?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G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整体折射。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法律制度也在发生演进。正如著名法史学者黄源盛先生所言,“时代的巨轮是不断向前的,社会每向前跨进一步,制度在形式上或实质上都要随着调整或推移,也必须导入许多新的思潮和新的作法。否则就会降低制度的功能,甚至僵化”[1]。虽然中国古代已有关于“禁言”“禁书”的部分法律文字,但是并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专门法律规定,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新闻出版法规的出现是在近代。年7月,自首颁《大清印刷物专律》迄今,中国新闻出版法规历经清末、中华民国、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重大历史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中,新闻出版法规都带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时代特点,也回应了当时新闻出版管理、权利保护等不同法律主体的利益诉求。当下,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闻出版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亟须法律制度层面上与时俱进的保障。观史可鉴今,综合研判中国新闻出版立法百余年的历史,把握制度演进的规律,总结规范变迁的经验教训,将对当下新闻出版法规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2]一、雏形初显:“清末修律”时的新闻出版法规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地位发生根本动摇。《马关条约》“使中国丧失大片土地,而且规定中国必须向日本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战争的结果不仅是清朝两百余年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也使中华民族遭受了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3]。同时,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国家和民族的蒙难更加激起了国人自强复兴的愿望。公车上书后,维新思想不断传播,报刊作为思想传播载体愈发为人们所重视。在年5月2日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直言,“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4]。梁启超更是撰写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阐述报刊的重要作用。据统计,自年8月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创刊到年9月戊戌变法之间,全国报刊增长到了七十多种,办报地区也由沿海延伸到长沙等中小城市,有力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也形成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5]报刊蓬勃发展之际,制定“报律”的必要性自然凸显。通晓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的康有为,年8月9日给光绪帝上《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的附片《请定中国报律》中特别提出制定“报律”。他说:“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书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缮写进呈御览审定后,即遵依办理。”光绪帝阅折后,同意了康有为的奏请。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慈禧太后以“莠言乱政”为由,下令停办全国报馆,严查传播维新思想的报刊。一时间,国内报刊数量锐减,制定“报律”的工作也戛然而止。[6]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除弊革新已经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之后,为了应对愈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清廷在年不得不发布“变法”上谕,开启了考察西学、官制改革、预备立宪、变法修律为主要的改革运动。制度的变革与思想的传播是相互促进的。作为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报刊在这一背景下又迎来了新的契机,“报禁”事实上也有放松。从内容上看,既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天南报》《文兴报》《益友新报》《新中国报》《日新报》等宣传“保皇改良”的报刊,也有革命派孙中山、于右任、陈其美等创办的《中国日报》《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中国公报》《光复学报》等宣传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报刊。报刊的日益繁荣,配合除弊革新的思潮愈发兴起,言词激烈者层出不穷,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舆论挑战。特别是年,在面对“沈荩案”和“《苏报》案”时,因为没有专门新闻出版立法,清政府处理起来十分被动,遭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由此,进行专门的新闻出版立法已经呼之欲出了。年末,徐世昌上奏《请饬纂订报律折》,明确提出:“奏为京外日报日多,亟应纂订报律,以示限制恭折。”年,作为出洋考察五大臣的载泽归国后,呈上《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其中也专门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主国现行条例,变为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7]年清政府颁发“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的基本国策,变法修律开始加速。相应的,专门的新闻出版立法也正式启动。总体来看,针对新闻出版事务,清政府专门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年6月)、《报章应守规则》(年10月)、《报馆暂行条规》(年9月)、《大清报律》(年12月)、《大清著作权律》(年12月)、《钦定报律》(年1月)等多个专门的法律法规。这些新闻出版法规颁布的时间普遍早于民法、刑法、商法等清末修律的重要部门法,虽然仍带有浓厚的封建法律色彩,但是已经具有近代法律形式与内容的“雏形”,对中国新闻出版法规迈入现代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概而括之,这些制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出版法。年6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签订的《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制定规范出版活动的专门法律。《大清印刷物专律》分为大纲、印刷人、记载物件、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共41条,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印刷物的注册登记、禁载事项、毁谤与教唆以及违律行为的惩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大清印刷物专律》涵盖了所有的文书、图画等法律对象,约束了著作、印刷、编译、发行、分售等众多出版性从业人士,是清政府针对包括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等事务进行管理的专业出版法。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制定了一些针对特殊领域的出版法。比如,为了规范小学、中学以及师范学堂等使用的教科书编写、翻印、出版等活动,从年到年间,学部还颁布了多部《学部审定教科书凡例》,陆续规定小学、中学、师范学堂等教科书,并开列了附书目表。其二,关于新闻法。随着国人再次办报高潮的来临,面对众多报刊,一部《大清印刷物专律》是不够的,需要更细致的专门规范报刊的新闻法。年10月,巡警部拟订颁布《报章应守规则》,专门对报刊活动进行规范,却只有九条,多为“不得……”的禁止性规定。为弥补《报章应守规则》的不足,巡警部于年9月又出台了《报馆暂行条规》。后者仅有十条,与前者多条重复。总的来看,两部新闻法内容粗糙,条文简单,并不能适应蓬勃兴起的国人办报活动。基于此,更加完备的“报律”呼之欲出。年12月,《大清报律》在巡警部、民政部、法部三个部门合奏的基础上,宪政编查馆再次复议,最后奕劻、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六大臣共同审议修改而成。《大清报律》是一部近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新闻法,共有45条,涉及报馆的开设、变更条件,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条件,稿件查核,禁止刊载事项,相应处罚方式,以及相关程序等内容。《大清报律》实施三年后,鉴于法律执行中有些不适应现实的情况,清政府于年1月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制定出《钦定报律》,共38条正文与4条附条。与前者相比,后者内容大同小异,并未做大幅改动,只是部分条款略有放松。其三,关于著作权法。著作权问题,是新闻出版法规中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于年12月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等5章,共55条。该法定义了著作权,并对其保护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附《著作权呈请注册呈式》《呈请继续著作权呈式》《呈请接受著作权立案呈式》等公文样板,对清末新闻出版法规进行了重要补充。二、博弈抗争: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出版法规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华民国的正式成立。直到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民国经历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阶段,国人长期压抑的新闻出版需求得到了充分释放,新闻出版行业与清末时期相比有了“井喷式”的发展。仅中华民国元年,全国报纸就“增至多家……从年2月到10月,8个月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北京报纸达80家之多”[8]。其后,新闻出版业更是迎来了重要发展。相应的,对于新闻出版业的规范性法规也展现出频繁废立修订的立法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宪法条文表面虽然载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但是在新闻出版法规条款的背后却彰显出民众对中华民国不同阶段政府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博弈与抗争。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既有临时政府创立的官报《临时政府公报》,也有政党团体的机关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等,还有商业性新闻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在这一短暂时期,报刊数量众多,又有不少图书出版,但是并没有特别系统的新闻出版法规出台。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法,在第六条第四款专门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同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还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仅有三段文字简要规定了新闻杂志的出版注册事宜以及“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调查失实,误毁个人名誉者”两种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但是,《民国暂行报律》一经出台,就遭到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的一致反对。作为国内第一个全国性新闻界团体,中国报界俱进会都出面发表了致孙中山大总统电,直言“报界全体万难承认”。为了巩固中华民国新生政权的稳定性,仅三日后,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明令撤销《民国暂行报律》。另外,为了应对著作权的相关事宜,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还颁布了《著作权呈请注册暂照前清著作权律分别核办通告文》,认为“前清著作权律,尚无与民国国体抵触之条,自应暂行援照办理”[9]。在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报刊、图书出版,甚至新闻广播都发展迅速。《亚东新报》《民族报》《中央新闻》《民生报》《国民杂志》《民国日报》等新办报刊由同盟会支持。除原有商业性新闻报纸外,又有《京报》《公理日报》《世界日报》《民立报》等商业性新闻报纸得以新办。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热血日报》等马克思主义报刊也得以新办。年12月,美国人奥斯邦还在上海外滩架设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新闻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广播电台”,年10月,刘翰筹建了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座新闻广播电台,随后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北京无线广播电台、沈阳无线广播电台先后播音。北洋政府时期,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严重,所谓的共和政体却带有浓厚的军阀利益。面对新闻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北洋政府选择的是制定一系列相关的新闻出版法规,并以此为工具实施强大舆论压制,甚至炮制了“癸丑报灾”这样的中国新闻出版发展史上的灾难。在《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中,都以宪法性条款的形式先后规定了“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在新闻法方面,袁世凯政府于年4月2日颁布了《报纸条例》,共35条,对报纸的定义、分类、发行、审批、禁载事项以及违法处罚方式等内容进行规定。年7月10日,进行了修订;年7月16日,段祺瑞政府对条例进行了废止。在出版法方面,袁世凯政府于年12月5日颁布了《出版法》,以《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为基础,经少量增减而成,共23条。这部《出版法》与前清时期的同类型相比,除了登记机关变更、惩处力度有所不同外,还有如下变化:第一,取消了注册费和保押费;第二,明确了出版关系人,即著作人、发行人、印刷人;第三,明确了集体著作的禀报方式:以学校、公司、局所、寺院、会所等名义出版的文书图画,由学校等单位禀报。这三点也成为后继出版法的通例。[10]这部法律是第一部以“出版法”命名的法律,在中国新闻出版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洋政府还制定了《管理印刷营业准则》《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教科书末页附印部令及规程摘要》《禁止翻印本部审定之教科用图书》《释藏经版保管规则》《释藏经典颁给规则》等出版方面的法规。在著作权法方面,北洋政府于年11月7日颁布了《著作权法》,年2月1日颁布了《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年10月3日颁布了《内务部通咨各省解释著作权法与出办法之差异请转饬切实办理文》,对新闻出版著作权问题进行了规定。除此之外,北洋政府于年2月5日还颁布了《新闻电报章程》,对新闻电报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闻出版行业发展又有了新的特点,代表各方利益的报刊、广播、通讯社等加速分化。以“一报”(“《中央日报》”)、“一社”(“中央通讯社”)和“一台”(“中央广播电台”)为主干的国民党党办中央新闻体系占据了大量物力人力资源和新闻舆论资源。除两次国共合作之外,长期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先后出版过《布尔什维克》《实话》《红旗日报》《党的建设》《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大公报》《民生报》等商业性新闻报纸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另外,其他政党、团体也有不少相关报刊推出。然而,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地位的强化,通过立法形式对新闻出版行业的管控力度不断增强。有学者评价,自年—年“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22年间,制定了大量的出版法律、法规。总体而言,对出版事业严加控制,呈现了一个由松到紧的过程”[11]。从法理上看,新闻出版立法的趋紧,其直接结果就是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压制的强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对压制的反抗。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闻出版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对于立法利益的博弈和抗争十分凸显,这特别体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新闻出版法规体系的基础性法规——《出版法》的反复修订过程之中。年12月,在中原大战刚刚平复,国内政局暂定之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专门针对新闻出版业的《出版法》。[12]这部《出版法》共6章、44条,将出版品分为新闻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三类,在注册登记等内容上予以区分对待。特别是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首次在中国新闻出版立法上对出版品的禁载事项予以专章规定。“年《出版法》所涉及的限制比照之前北京政府《出版法》,限制内容更宽泛,特别增加了国民党党务、党义方面内容的限制。这部《出版法》与北京政府《出版法》相比,在登记机关发生变更和惩处力度上也有不同的差别,而且更加具体化。”[13]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还公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对《出版法》的进一步施行予以细化。然而,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出版法》一经出台便引发新闻出版业的反对。“据统计,自该法公布实施到年12月,各省请求释疑者达30余件。业界对《出版法》有意见,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也对《出版法》的不完善提出质疑,意图对其进行修改。”[14]虽然立法修改是共识,但是出发点却截然不同:新闻出版业为了争得更大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国民政府则为了更好地钳制新闻舆论。这种立法宗旨的对立化为《出版法》日后反复修订埋下了伏笔。年7月,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修正出版法》,正式将议案提交立法院审议。随后,立法院例会讨论通过了该议案。由于广受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zhejiangzx.com/zjxw/10254.html |
------分隔线----------------------------
- 上一篇新闻: 浙江日报聚焦一块布里乾坤大柯桥加
- 下一篇新闻: 没有了